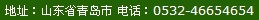|
上周日是母亲节,敬一丹在王府井携新书《床前明月光》与读者见面。这本书是写母亲的。活动开始前,敬一丹接到女儿的视频来电祝她母亲节快乐,她却恍惚了。年年为母亲庆祝,她还没有从女儿的角色中转变过来。愣了一下她才忽然意识到这个事实——母亲已经去世一年了,自己没办法再说“母亲节快乐”了。 ▌医院病房。 4月27日,敬一丹过了65岁生日。这个生日她过得很艰难,因为这一天也是母亲去世一周年的忌日。母亲去世那晚,她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妈妈要在自己生日这天离开。她想,以后再也不过生日了。亲朋开解说,这是因为母亲太爱你了,是生命的缘分,以后就过农历生日吧。之前央视的同事李小萌安慰她,这是你从精神上脱离母体,成为独立的人,迎来的又一次新生。她听进去了,这样的解释让她好受了些。 《床前明月光》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为亲爱的妈妈送行”,“送行”这个词是敬一医院看望赵忠祥时,白岩松提到的。如今,她开始感觉到这两个字的分量。 ▌《床前明月光》敬一丹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生死是沉重的话题,尤其是父母亲人的生死,我们的文化里似乎忌讳生命的终结,总希望生命可以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暂时没发生的事情就当不存在。敬一丹的母亲查出癌症时,四姐弟决定不告诉老人。许多病人家属都经历过这个煎熬的过程,告诉还是不告诉?敬一丹的母亲干了一辈子的公安工作,明察秋毫的性格让她对自己的病情早就心中有数,也理解儿女的隐瞒。母亲在三亚的泳池边面对面直接问敬一丹:我是不是喉癌?听到“癌”这个字,敬一丹心腾地跳了一下,但她发现母亲远比她想象中镇静和坦然,母亲对她说:“行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该走了”。 ▌敬一丹和母亲在三亚的泳池边。 敬一丹的女儿是80后,她知道姥姥的情况后,不同意敬一丹的隐瞒。她推荐敬一丹看一部电影《别告诉她》,电影探讨了病人有没有知情权的问题。敬一丹发现自己这一代习以为常的想法正在被年轻人质疑,年轻人似乎并不那么避讳生老病死。 “我姐姐的孙女从小就跟着我妈妈生活,和她特别亲密,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她才四岁半。”敬一丹有些惊讶小姑娘的父母没有避谈死亡,而是直接告诉她什么是生和死,什么是土葬,什么是火葬。敬一丹告诉笔者,她咨询过教育专家,在孩子多大时可以谈论死亡,得到的答案是,四五岁就可以了。小女孩的父母是有现代思维的年轻人,敬一丹相信在她以后漫长的人生中,这次经历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以后她会面对很多事情,而这颗种子总会起作用。“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经历过生命教育的,多少人面对生死的时候会缺少心理准备,现在中小学的这种教育也是缺失的。很多成人都需要补这一课,我也需要补课。” 敬一丹在央视做新闻调查节目时,曾采访过关于临终关怀的选题。“所有的孩子在那个时刻都有无力感,我就看着妈妈在痛苦中煎熬。面对至亲的最后时刻,我们怎么能判断出,该结束了呢?你会跟医生谈这个话题吗?我没有谈过,但我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的时刻。”敬一丹想知道如何在明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如何与病人交流,如何在度日如年中与亲人告别。 在读者见面会上,敬一丹请来了重症医学专家朱立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王博探讨在当下的现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从疾病到死亡的过程,尤其是一个在大众看来还很陌生的概念“生前预嘱”。“生前预嘱”在国内也被称为“预先医疗指示”或“预立指示”,是指立预嘱者在其意识清楚时签署的,就其处于生命末期时是否需要采用生命支持手段或其他延缓生命的医疗措施的事先说明。因为还没有相关立法,实际执行中也面临着种种复杂的情况,目前在国内还在逐步完善中,人们对此的认知了解和观念转变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采访结束后敬一丹告诉笔者,第二天她就启程回三亚陪父亲。父亲已年过九十,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当父亲问她叫什么名字时,敬一丹心如刀绞。现在她已慢慢接受父亲开始不认得自己的事实了。尽管最终会什么都不记得,还是要陪伴。 “我这个年纪已经感受到夕阳了,但我前面有了母亲这样一个变老的示范之后,现在就比较平静看待这件事了。”敬一丹说,中年和老年之间的岁月中人会产生很多惶惑,“五六十岁的人是很害怕变老的,这是一个坎儿。” 敬一丹在五年前退休时读到一首诗: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现在再读这首诗,她有了更深的理解。她情不自禁在诗的最后又加了一句——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变到像妈妈期望的那么好。 父母有潜在的欲望 书乡:您的母亲生活在哈尔滨,最后是在三亚去世的,这是她的愿望吗? 敬一丹:是她想去的,(之前)每年都像候鸟一样过去。但是那时候已经放疗完了,这趟去了很可能回不来了,其实到了那时候,哪儿的医疗都没有办法治,已经到晚期了。最后她是在三亚告别的,她喜欢这样的环境。她从发病到去世一年半,中间走过两个来回,回到东北是坐火车,再来三亚是飞来的。那时候病有点重了,但其实是我们成全了她的愿望,她很想坐一趟火车。我小弟陪着她一路,车窗外全是风景,她很满足。 书乡:父母临终时除了满足他们的愿望,子女还可以做哪些事? 敬一丹:我妈走的时候是没有遗憾的。她把所有的愿望说出来。其实父母是有些潜在的欲望的,比如他们心里是需要得到肯定的,这不是一个具体的愿望,不一定能够表达出来,但我们要读出这些。年轻人不太能意识到,觉得老人也需要激励吗?他们需要这种力量,尤其是在无力的时候。 书乡:有人说父母去世后,自己跟死亡之间的遮挡就没有了,要直接面对死亡,这件事给您最直接的改变是什么? 敬一丹:我这次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原来妈妈在夕阳里,妈妈走了以后,我就站在夕阳里了。我面前有一个巨大的精神空缺。我用了很多方式劝自己要接受。接受这个词说起来容易,但内心就是有这样的空缺。未来的路我得自己走。失亲之后会有很多心理调适。这本书原来没有后记,交完书稿疫情就发生了。我就加了后记。后记写了两个月,疫情在不断变化,很多人都有失亲之痛,所以我就更想让这本书,能与更多人交流。 ▌敬一丹(右)和母亲 慢慢接受医疗的有限 书乡:医院时有心理医生来,医院派的? 敬一丹:医院派的,三亚的医院。可能重症就会派心理医生去看一看。当时心理医生来就说:这老太太没问题。我妈不会说痛苦就露出不行了的样子,她是有精神力量的。他看我们家属情绪挺低沉的,就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自己成为病人啊。在医院的环境里,人的心情更容易变糟,焦虑,绝望。我也想了一些方法去调整自己,让自己尽量过正常的生活。 书乡:您怎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敬一丹:原来觉得要不惜代价治,后来我就慢慢地接受医学是有限的。这是从纠结到接受的过程,接受医学的有限,接受生老病死是不能改变的。 书乡:书中写的母亲身上插了11根管子,而一开始她一根管子都不愿意接受。您怎么看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 敬一丹:妈妈走了之后我看她
|
当前位置: 喉癌疾病_喉癌疾病 >直面离别,敬一丹说妈妈走后,我就站在夕
直面离别,敬一丹说妈妈走后,我就站在夕
时间:2023-4-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西班牙安乐死合法化前的38年中国生物技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