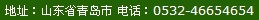|
1 司机老王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大大咧咧,自以为是,在我们这个小国企,人人都知道他的坏毛病。有年轻女同事坐在车上,他旁若无人地对着窗外的村姑吹口哨,感慨道“少年不知精子贵,老来望×空流泪”,然后哈哈大笑,我们只能尴尬地默不作声。 偶尔说起工作上的事,他全情参与、频繁搭腔,说恼了,总结一句:“领导都是复读机,中层都是三明治,我们只能白受气”,万籁俱寂,颇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等到真正有领导坐在车上,他更是信口开河、百无禁忌。什么话题都要掺和几句,而且还听不得反对意见。有一次,公司总工张总坐车去下面的工地,拿出图纸,想抓紧时间和后排的技术人员定一下塔吊的规格。说了一会没主意。老王手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轻描淡写地发表意见。 “臂长绝对不能低于40米,0.8吨的够用了,这么明显有什么好商量的?” 后面还坐了位分包老板,在一旁偷偷地笑,刚被提拔,不到四十岁的张总工脸上有些挂不住。 “你又没看过图纸,你懂什么?” “我不懂?当年修四十多层的城市大厦,几位德国专家都是我陪着讨论方案,怎么挖基础,怎么搭钢管,怎么封顶,我到现在都背得出来。那时你们几个还在院子里擦鼻涕玩泥巴呢。” “光凭过去的老经验也不行啊,现在新技术那么多。” 争执的结果,是老王被彻底激怒。他把车停在高速路应急车道上,要求张总工立即下车。 “下去!我的车你不配坐!” 总工满脸通红,后面几位打着圆场。 “算了,老王,都是同事嘛。” “是啊,我们讨论技术问题,又不是说别的。” “就是不行!你们把图纸摆在我旁边,影响我安全驾车,万一出事了,谁来负责?公司领导就可以破坏安全吗?” 当时正值处暑,年轻的张总工在高速路上顶着烈日,徒步行走了整整三个小时,才等来小车班派过去接应的另一辆车。据说这成为该领导人生仕途上最猛烈的一次打击,从此留下心理阴影:再也不在车上讨论任何技术问题。 2 我要到下面一个小城市去参加个培训,小车班安排了老王送我。知道他的火爆脾气,车上也只有我们两人,便起了个外地狎妓猎艳的话题,瞬间开启了他的话匣子,地域跨越东西南北,甚至延展到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讲得唾沫飞溅滔滔不绝。正说到兴头上,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 他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拿起手机贴到耳边,丝毫不顾惜乘客的生命,我却只能敢怒不敢言。结果没说上两句,他自己先恼了。 “我在开车呢。什么?知道了知道了!上个月钱转了嘛,这个月发了工资马上给!别说那些,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会欠!” 挂了电话,老王还在气头上,鼻孔一张一合,直直地看着前面。为了车辆和自身安全,同时也怕经历与张总工一样的遭遇,我决定缓和下气氛。 “怎么?买了新房子啊?这个时候买房选得好哟。” “买什么房,谁还买得起房啊?我还我爸的钱。” “刚才是你爸?他们还在老家吗?” “都在城里,他们可比我过得好多了!” “那还欠什么钱?” “还不是我之前的老婆留下的。” 老王把话题拉回到二十年前。 那时的老王还是小王,从小学读到初中,成绩永远拖后腿,一身蛮力加上牛脾气,很快便成长为学校里的混世魔王,跟着一群坏学生打架滋事、横行霸道。 初二时,与邻近乡镇的学生约了一架,在校园后面的小树林打得天昏地暗、拳拳到肉。 混战中,一位外镇少年不知被谁捅了一刀,刀刃距离肝脏不到两厘米,当场血流如注、痛苦哀鸣。镇政府、派出所、医生全部到场,在场人员全部收押。一经审理,结果伤人方——也就是小王他们的“领军人物”正好是镇委书记的儿子。 于是赶紧向上层报告,家里也是八方托关系求情,最后付出巨额赔偿,把案情修改为“擅自奔跑,跌倒撞上新锯树桩,碎木屑刺入胸腹,幸未伤及内脏。”被刺的本是个贫苦孩子,收了钱不再言语,学校也乐得个清静,这事就算是了了。 第二周,班主任把小王他爸叫到办公室,几乎是低声细语地恳求,你们家长申请办退学吧,让他去工作挣点钱,别再出来祸害社会了。学校甚至可以为逃过义务教育给予经济补偿。他爸也怕他再在学校里制造麻烦,干脆直接拎回家,从此开始了社会大学的学业。 结果,犹如小鱼放进了大海,野马牵回到草原,哪里还把持得住? 跟着一群地痞在街头胡混,除了杀人放火之外,够不上刑事犯罪和特大要案的坏事基本做了个遍。 晃荡了两三年,小王他爸实在看不下去,赶着去驾校考了个证,先是给找了个开出租的工作。 结果他把车停在茶馆外面,进去参与赌博,玩“推对子”,眨眼功夫把钱输得精光,每天的规费也交不出来。 出租车公司的领导出于好心教育了几句,他一气之下,直接辞职不干。 他爸找不到其他办法,挣扎着又凑钱买了辆旧捷达,他也只有开车这项技能。便开始偷偷拉客,法律术语叫“非法载客营运”,俗称“野猪儿”。他倒是喜欢开着车在小城里游荡,加上年纪也渐渐大了,逐渐也消停了不少。 3 那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如日中天,很多小城市里都开办了规模庞大的纺织厂,而手工为主的性质,又决定了其中多以年轻女工为主,俗称“丝妹”。 每天上班,纺织厂门口就涌进来一群青春热情、五彩缤纷的美丽少女,一到下班铃响,这些少女又叽叽喳喳欢闹着,像一群小鸟飞出厂门,飞向小城各个角落。这幅场景令年轻的小王心神激荡,也蕴含着非法营运车辆的巨大商机。 因此,小王第一次热爱上了载客运输这项职业,每天守在纺织厂门口,女工们追时髦、爱攀比,加上小王这样的俊俏后生,三两下便混得熟了。也就是那个时候,小王遇到了阿红。 “浪荡子和丝妹的爱情故事?”我打趣道,谈起往事多有几分惆怅,车厢内的气氛也缓和了许多。 “小时候哪里知道什么爱情,那股劲头跟种猪往母猪堆里钻差不了多少。”对于许多正人君子,“丝妹”是一个暧昧然而不洁的群体,她们过于妖娆放荡,甚至敢于在夏天时呼朋唤友一同到河里游泳,虽然身着衣衫,但已经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而对于小王这样的浪荡少年,丝妹又是极易上手的代名词。“野猪儿”团队整齐排列在纺织厂门口,热情招呼、殷勤拉客,上车后又没话找话、百般挑逗。不久后,便有师兄开始炫耀与丝妹上床的战绩。 小王也想着勾搭几位,但苦于性格爽真、口无遮拦,常常在关键时刻言语粗俗,搞得后座的丝妹笑容消失、脸色下沉,直到冷哼一声,甩门便走。小王为此懊恼不已,却又求师无门,只能暗自懊恼、苦不堪言。 阿红在众多丝妹中显得很独特。她从不搭乘野猪儿,因为有一辆车专门接送她上下班,如此待遇可算作是丝妹中的翘楚。 但她并不快乐,上车下车都没有笑容。一大群少女欢喜笑闹,与年轻司机一边打情骂俏,一边乘车赶往热闹城区时,她只是冷冷地站在路边,静静等待她的专属司机。 小王把车排在队伍的尾巴上,然后慢慢往前挪,这个时候,他便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阿红,渐渐地,他也对这位沉默的女人产生了些许好奇。 有一天,阿红没有等车,而是径直走到了小王的破捷达旁边,也不多话,拉开门坐进后座。说了一句“常明桥”,便淡淡地望着外面,再不多说。 小王先是怔住,习惯性的启动转头,往常明桥方向开,走了一会,实在憋不住了。转头搭讪:“美女,专门来接你的车呢?” “不来了。” “和男朋友分手了?” “专心开你的车。” “别人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有什么烦心事说出来就好多了嘛。” 后座再无回应,小王又说了几句,只得讪讪地住口。 下车时,阿红问多少钱,小王说八块,阿红掏出二十,对他说:“从明天起,我每天给你二十,到这个时候准时在厂门口见。” “哦,知道了。”小王接过钱,想开句玩笑,不知道怎么开口。阿红看看窗外,漠然的下车,消失在漆黑的楼梯门洞中。 从此以后,小王便成了阿红的专属司机。每天准点停在厂门口,有师兄问起小王就对着别人憨憨地傻笑。亲密关系迅速传遍了江湖。有人私底下议论,说稚嫩的小王是完全被这位老江湖给玩弄于股掌之中。 持同样态度的还有小王的母亲,她天天在老伴耳边吹风。把他父亲也惹恼了,饭桌上要求:不准再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丝妹接触。 对正值水深火热的小王来说,这些话只当耳边风。父亲气急了,顺手抄起暖水瓶用力砸过去,小王身手敏捷,侧身一躲。暖水瓶把一扇报纸糊的木窗砸出个大洞,留下几块纸角和碎木屑在风中凌乱。 外面闹得沸沸扬扬,兄弟们看过来的眼神也充满各种意味,但只有小王明白,他和阿红其实什么也没发生,就只是最单纯的雇佣关系。而且阿红对自己的事情讳莫如深,基本不跟小王搭腔,仅仅偶尔下车时,出于对小王遵守诺言的感激,才轻声说句谢谢,或是微翘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这个安稳的局面在两个月后被打破。其实在距离几百米的时候,小王就注意到了那个男人。 阿红的家在小街的右侧,平时僻静少人,加上小城人民夜生活单纯枯燥,下班时这里基本没有什么人出没。 但那天刚刚过转角,小王便看到男人站在路口,叼着烟东张西望。他把车停在街口,看着阿红下车,走进小街。两个月来,他已经习惯等阿红走入楼梯门洞才离开。 阿红下车走出不到百米,男人便丢下烟朝着她走了过去。凑近交谈,被阿红推开,男人被激怒,挥舞着手臂吼叫,阿红充耳不闻,匆匆地往前走,男人拉住她的手臂,被甩开,再把手臂牢牢抓住。阿红挣扎起来。 小王坐在车上,隔着玻璃看着事态进展。他没有立即下车的原因,是他看得出来这并非一起简单的骚扰,男女背后还埋藏着感情。但挣扎的阿红无疑点燃了他的勇气。小王拉开车门走出去,指着男人大吼了一声:“快放手!” 那男人先是一愣,接着猥亵地笑着,说:可以啊!会养小狼狗嘛。还说没钱?一日夫妻百日恩,舍得花钱喂小狼狗,就舍不得拿点来救我的命? 这副流氓嘴脸,小王从不陌生,此时说任何话都是多余,小王加快脚步,对准男人的脸就是一拳。男人嗷嗷叫着扑过来。 小王一把抓住他的左手腕,迅速往后一别。这男人也有些实战经验,就势一蹲身子下沉,躲过了这次压制,右手不知从哪里抽出一把匕首,转身一划,在小王的手臂上瞬间拉出一条长长的口子,鲜血马上涌了出来。 小王咬着牙忍住疼痛,继续用手钳制住他握着匕首的右手,在墙壁上狠狠地撞击,解除武装后,又用身体牢牢地压下去,扭曲的手臂引发剧烈疼痛,男人只好哀鸣着求饶。小王威胁他,如果再敢来骚扰阿红,就是直接在身体上卸零件的问题了。 男人连声说好。小王又狠狠地扇了他几记耳光,这才把他放开。男人立起身子,看了看阿红,又看了一眼地上的匕首,没胆子过去捡,只好转头离开。 小王说你先上去,我去医院包扎下伤口。阿红捧着他流着血的手臂,叫小王上去,由她来包扎,同时也怕男人再来骚扰。小王没有理由拒绝这个邀请,于是便跟着上楼。 在阿红干净、整洁,同时散发着淡香的房间里,她仔细帮小王清理伤口、上药包扎。 也许是突发事件终于打开了心扉,她开始讲起和男人的往事。那是她的前夫,结婚前一切都好好的,婚后跟着亲戚出去打工,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先是在城市里搞得入不敷出,最后被工厂辞退,回来后不思悔改,天天呆在茶馆的包间里同人炸金花、扯马股,后来竟然还染上了毒瘾,阿红苦劝过、苦恼过,终究无济于事,找了些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亲戚,加上政府人员出面调解,好歹把婚离了。 父母留下的积蓄被耗光了,男人便回过头来,打起了阿红的主意。在纺织厂手工缫丝的那点收入,怎么抵得过烂赌和吸毒的挥霍?之前男人把家里的三层小楼卖了出去,如此支撑了两月,房款耗尽,毒瘾发作,男人只好放下一切尊严和人格,再次四处找钱。前几次阿红还拿出少量现金应付过去,后来便越发猖狂。 伤口包扎完毕,才发现两人的衣服上都沾上了一些血迹。阿红说赶紧给漂洗下,不然等干了就洗不掉了。她让小王站起,把受伤的手缓慢地举起来,然后抓住白色衬衫的边缘,往头上脱下来。他的胸膛感受到了她呼吸出的热气,痒痒的让人想笑。 然后她又走到衣柜那边,拉下蓝色连衣裙的拉链,文胸带子和顺滑的后背暴露在空气中。小王觉得体内的那团火轰的一声骤燃起来,瞬间烧掉了他的整个身体和全部理智。 4 当小王带着被纱布包扎的伤口和一身满足的疲乏回到家时,迎接他的并不是势不两立的父亲,而是母亲和一位远房表叔。这位表叔已经在大城市里成家立业,据说混得风生水起。看他打了摩丝的头发和泛着油光的皮夹克也能瞧出些许。 两人并没对他的伤口表达过度关切。而是迅速说起了小王的未来。这位成功人士此次回家不仅带了一些只在大城市能够吃到和买到的东西之外,最大的礼物是为小王带来了一份工作:给一位老板当司机。不仅包吃包住,接送老板还会有一些外快。每个月工资起步五千元。 五千!这是小城镇里很难想象到的金额。小王就算不吃不喝,在小城里每个月能赚到两千就算是顶天了。而对于他的父母,这个工作更是他离开家乡,离开狐朋狗友和什么丝妹的最佳选择。 表叔又说,有这个机会,主要是因为老板前一个司机遭遇车祸,暂时无法开车。所以要得紧急,一旦决定必须当晚便走。这后一句则是来自于父亲的授意,跟着小城流氓和不良少女只有把自己彻底毁掉。他巴不得小王立即消失,到大城市去闯荡出一番事业,再回来光宗耀祖。 最终,小王没能克制住自己对大城市和这份工作的向往。他甚至来不及跟朋友们告别,便跟着表叔踏上了前往大城市的漫漫路途。 小王的性格根本无法适应伺候老板的工作,待遇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干了不到一个月,小王便被老板辞退。于是东奔西走,到处找机会,什么草坪修剪护理,高楼外墙保洁,超市搬运库管等工作干了一大堆,最后落脚到我们这个小国企,方才安顿下来。 有一日,小王陪着他在公司招待所当服务员的女朋友一起逛街,小情侣卿卿我我,吃小面、看电影、挑衣服,无聊却也幸福满满。正在兴头上,突然对面走过来一个女人,指着他的鼻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你还好意思这里逛商场,卿卿我我,你知道阿红这几年有多辛苦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小王一脸懵逼,阿红?辛苦?望着眼前这位怒气冲冲的女人,他认出是当年丝妹中的一位,同时依稀找到了一些往事的脉络。这位火爆脾气的女人只叫他赶快去找阿红,其他也没多说便匆匆离去,留下小王尴尬站着,不知怎么给女朋友解释。 当晚,他给父母和几位朋友打电话,都已失去了与阿红的联系,随后又四处联系,总算得到一个地址。第二天,他按照地址,到另一座小城里,寻找到了阿红目前居住的地方。 5、 那是在城郊一座僻静的小院,小王却没看到阿红,只见到一对老夫妇坐在门口吃饭,小桌上放着一碟花生米、一碟酸菜和热过之后看不出什么菜炒的肉片。 他向二人询问阿红,老妇人抿着嘴喝粥没有搭腔,像是有点耳背。倒是端着酒刚喝的老头子眯着眼,朝院坝中间努了努嘴,然后说了一句:她上班去了,诺,她儿子在呢。 小王这才注意到院子中央,还有一个孩子坐在地上玩泥巴,衣服上沾上了尘土,面前一片黑黢黢的油,像是已经结成硬块。小王道了声谢,便自己走过去,坐在一个小木凳上等。 时近深秋,坐在小院中已隐隐有些寒气,孩子贴在地面上,肯定更冷。但是老夫妇似乎对这小孩漫不经心。沉默着吃饭,只是偶尔朝这边瞥来几眼。 小王担心孩子被冻着,便唤他起来,拿起地上的几根树枝逗他。那孩子也不怕生,手支撑着从地面站起,摇摇摆摆地走过来。 一张脸被鼻涕、泥土和污垢涂成个花猫,孩子望着他笑,眼神清澈得像一汪湖水。小王突然鼻子一酸,忍住眼里的泪水。他想发出点声音逗弄孩子,结果一开口,发现声音里竟然有些哭腔。 先是另一位女工回家,还穿着服装厂的工作服。老夫妇同她窃窃私语了一阵,终于如释重负的推着俩三轮车出门了。那女工走过来,问小王:“你找阿红吗?你是她什么人?” 小王点点头,略略犹豫了一下。“朋友……一个朋友。” “哦,那你可能要再等一会,要不先到我那边喝杯茶?” “没事,我就在这里等她。谢谢你。” 那女人便不再多说,转身进了旁边一个房间。 又等了半个小时,阿红回来了。 她穿着和女人一样的工作服,有三年多没见,看起来却像比以前老了十岁。 小王把孩子抱着站起身。阿红看了他一眼,并不理会他和孩子,与隔壁的同事打了声招呼,就开门进去准备晚饭。他抱着孩子进了房间,看见阿红背对着门口在切菜,两个肩膀抽动着。他走过去,用另一只手环住阿红的腰,把脸贴在她的头发上,两个人这才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小王带着阿红和孩子回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只要在一起,生活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孩子上户口倒是费了不少周折,但比起其他苦难,这点烦恼算得了什么呢? “呃……你有没有想过去做个亲子鉴定什么的?”我小心翼翼地试探。 “就是你们这种读书人心眼多,只会搞些鬼名堂!有句话说得好,知识越多越反动,社会就是被你们这种人搞乱的!”此时的老王就像是被活生生拔掉胡须的狮子,一声呼啸令天地变色。 好吧,我默默地咽下自酿的苦果。 上天仿佛要存心捉弄这个小家庭。 没过几年幸福日子,孩子小学还没毕业,阿红连着几月觉得胸闷体乏,白天没胃口夜里睡不着。医院,阿红实在扛不住了才去挂号检查。一查就查出个乳腺癌,一开始还瞒着本人,但老王心里根本装不下事,三两句就被套出真相。 阿红也算是坚强,没有哭闹没有崩溃,咬着牙坚持化疗放疗,唯一放不下的只有孩子。常常在夜里拿出手机,对着孩子的照片流眼泪。 老王白天里上班,医院照顾妻子,请了位保姆随身护理,孩子只好由爷爷奶奶先接送和照顾。单位也充分考虑他的具体情况,尽量安排市内的人员接送,保证他每天可以回家。化疗不便宜,有些进口药打一针就要好几千,家里的积蓄很快耗光,单位上也组织了捐款,但还是抵不了花销。 有一天,医院送饭,回来的路上,孩子问他:“爸爸,妈妈会死吗?” “只要我们听医生的话,把病治好,不会的。” “那爷爷奶奶会死吗?” “爷爷奶奶?他们死什么?” “昨天吃饭的时候,爷爷说妈妈会死,还会拉着他们两个陪葬。说妈妈把钱花光了,一家人都只有陪着去死。” 老王一脚油门,以最快速度杀到父母家中。进了门,咬牙切齿、气势汹汹,手指着父亲的鼻子吼叫起来:“你有没有良心?当着小孩的面说这些!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都没说啊。” “别在这里装傻,我都听到了!” “把你的手放下去,你为了一个婊子,连老子都不认了吗?以前谈恋爱我就很反对,这种女人惹不得。看吧,过了这么多年,最后还要得个癌症,把我们都拖死。我和你妈还要养老,还要留棺材本!” “好!这些钱当我借你们的,我以后每个月还给你们!” 阿红也知道治疗仅仅是心理安慰。她忍着疼痛拒绝了后面的进口针和止痛剂。 在某个稍微缓解的夜里,她给老王讲了童年的一个故事,那是发生在她五岁的春节,家里来了一个靠贴福字到处乞讨的道士,她母亲舀了两碗米给他,那道士看到她,轻叹一声,转身离开。口中絮絮念叨:人强命不强,人强命不强啊! 目的地到了,老王的故事也讲完了。从此以后,每当别人在背后评论老王,我从未掺和过一句话。遇到车上尴尬的时刻,我还找些说辞帮他圆场。老王永远改不了他“讨人厌”的本性。但是资历在那份上,单位上也没人去招惹。 他和第二任妻子结婚的时候,严重高估了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到处洒请帖,准备了整整四十桌,结果到场的不到百人。 为了场面不至于太难看,大家自动往舞台和主桌围聚,父母席位上,只有女方母亲孤零零地坐着。老王站在舞台上满面喜色、声若洪钟,同样经历过一次婚姻的新娘幸福的依偎在旁边,根本没察觉到宾客的担心与尴尬。 此文为看点(小故事大感悟)原创内容,特此声明 白癜风专科北京白癜风医院哪里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ldfdj.com/haby/1633.html |
当前位置: 喉癌疾病_喉癌疾病 >妻子患癌症他倾家荡产治病,因为一件事他和
妻子患癌症他倾家荡产治病,因为一件事他和
时间:2016-11-2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科普如何预防喉癌
- 下一篇文章: 极品嫂子天天祸害我老公让我崩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