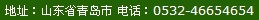|
俄罗斯人到底为何要喝酒?——书中也许有现成的答案。“俄国所有正直的人全都这样!……是因为绝望啊!是因为他们正直,是因为他们无力减轻人民身上的负担啊!”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我们的北方邻居称作“战斗民族”,很难说这个绰号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又有多少源自于固化了的思维定势。要亲眼看到“战斗”的俄罗斯人并非易事,现代旅游工业早已把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两京粉饰得有如波将金村庄,在行色匆匆的游客脑海中,留下的更多是文明、发达的欧式印象。不过离开的通道并未堵死,这便是连接两京及其郊外村镇的通勤列车。 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乘坐这种电气火车仍能给人一种相当前现代的体验,车厢陈旧,列车走走停停,低廉的票价引来大量都市底层游民,人满为患的车厢仿佛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实践场。小贩们往来车厢间贩卖各种奇形怪状的货色,前一位大妈还挥着电蚊拍和粘蝇条翩翩起舞,身后卖渔猎设备的大叔就已在展示有半节车厢长的超级鱼竿,仿佛要把那大妈吊出车外。你身边的醉汉硬是要把咬过一口的馅饼往你手里塞,并告诫你,若不吃上一口,就是“不尊重我、不尊重俄罗斯”,没过多久,他已毫无知觉地醉倒在车厢走廊上。查票员正眼开眼闭地驱赶逃票客,待走到醉汉身前,便熟稔地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瞳孔。“活着呢”,她轻巧地嘟囔一声,随即又投身对逃票者的追逐之中……
其实,俄罗斯的通勤列车一直就是未经规训的原始丛林。早在四十年前,就有一部小说瞄准了发生在电气火车上的故事,这就是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长诗”《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与作者同名的主人公韦涅奇卡(韦涅季克特的昵称)每周五都要离开和自己格格不入的莫斯科,乘通勤列车前往心中的伊甸园——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小镇佩图什基与情人相会。 他一路纵情狂饮、谈天论地、嬉笑怒骂。酒精自然是一切混乱的催化剂,书中提到的酒精饮料有几十种之多,啤酒、伏特加、葡萄酒、鸡尾酒——这可不是你在酒吧里喝的半水半酒的小资玩意儿,在小说里提到的鸡尾酒配料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工业酒精、净化上光剂、脚汗药、醇溶清漆、花露水、去屑喷雾、酚醛树脂胶水、刹车油、专灭小型昆虫杀虫剂(78-82页,译本中的讹误处直接在引文中更正,不再一一指出,后文亦然,有兴趣的读者可略作比较)。别以为这是作者异想天开,这些正常人心目中的毒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含有大量乙醇,因此它们在俄罗斯几乎都有悠久的饮用史。
小说的作者叶罗费耶夫就是个酒鬼。他出生在北极圈外科拉半岛上的一个小村,父亲是附近小火车站的站长。小叶罗费耶夫七岁时,父亲因酒后胡言被判流放,母亲无力独自抚养孩子,就把他们统统扔在了孤儿院里,远走高飞。然而,叶罗费耶夫从小就展现出对语言文学的极大天赋,中学毕业后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莫斯科大学。然而进入这所苏联顶尖学府后,他很快厌倦了学校的课程,并开始酗酒。尽管老师都十分赏识他的天才,尽力想保护他,可不领情的叶罗费耶夫最终仍被开除。他的许多同学(如穆拉维约夫、阿维林采夫)后来都成了杰出的文学研究者,可叶罗费耶夫却注定要浪迹天涯。 离开莫大后,他又考上过多所院校,每到一处,都因渊博的知识和洒脱的生活方式而深受欢迎,但很快他都会因为摊上这样那样的麻烦而被学校开除。最后,叶罗费耶夫成为了一名电话排线工,每天的工作内容就如同小说里描述的(35-37页):排电缆、喝酒、赌钱,第二天把前一天排下的电缆捞起来扔掉……他有一批固定的酒友,他们常坐在来往莫斯科和佩图什基的通勤列车里,饮酒斗诗,一直喝到不省人事。这部小说原本是他随手写来供朋友传阅的,不料传到了海外,年以色列一家出版社将其出版后,西方国家纷纷跟进,叶罗费耶夫的名字也渐渐在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圈中响了起来。
地位的改变并未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叶罗费耶夫照旧没完没了地喝酒,甚至在朋友家投宿时,把别人家里的伏特加、花露水连带存款一并喝光。年,他被确诊患上了喉癌,手术夺去了他的嗓音,但却无法让他放下酒杯。年,小说在苏联国内出版,却极其讽刺地刊登在了《戒酒与文化》杂志上,此刻作者也已时日不多。尽管虔信宗教,但作家却始终和教会保持距离,当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圈还在争论他为何会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时,他又决定死后在东正教堂进行安魂祈祷。他的一生仿佛都在给人放烟幕弹、出谜题,难怪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大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曾说,叶氏本身就已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神话。
叶罗费耶夫一生著述不多,除了这部不长的小说外,还有若干剧本、杂文、笔记。据他自己所说,他最用心的著作是长篇小说《肖斯塔科维奇》,但某次醉酒后把手稿掉在了火车上。不止一拨心急火燎的文学研究者曾派出科考团,把莫斯科——佩图什基铁路沿线兜底翻了一遍又一遍,可至今仍一无所获。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所谓的《肖斯塔科维奇》可能只是叶罗费耶夫对世界开的又一个玩笑。
不管有心栽培的《肖斯塔科维奇》到底存在不存在,无心插下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却差不多已经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确立了经典地位。已有多位学者为小说撰写了详尽的注释,注释长度都几倍于正文,有关小说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就像叶罗费耶夫充满谜团的生平一样,这部小说也留给批评家大量自由发挥的余地,截然不同的各种意见都能找到坚实的文本证据。在许多不喜欢这部作品的人看来,小说无非就是对俄罗斯酗酒现象的自然主义描写,它能被译成那么多外语出版,无非因为小说内容十分猎奇,确证了西方对俄罗斯人的某些思维定势;也有人觉得这是一部道德教化作品,告诫人们酗酒的危害,叶罗费耶夫的主治医生就十分确信地表示,书中对酒后意识、行为的描写十分科学,具有“揭露性”——想必《戒酒与文化》杂志社的那位编辑也是如此认为的。
学界常把《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视作俄罗斯第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过去俄罗斯文学中和谐的世界图景在这里终于化为彻底的混沌,与之一起被打碎的还有小说的语言,除了叙述的无逻辑外,作者对引文、典故的大量使用、混用和歪用(戏拟)也打破了阅读的连贯性。靠着渊博的知识和化用语言的天赋,书中一些看似酒后胡言的语句,其实都有出典和深意,除了小说文本与外部文本的互文之外,小说内部的文本也紧紧勾连在一起。 比如在发现伏特加遭窃后,主人公抱怨道:“心地单纯的我在这一路上居然一次都没看车厢,这完全就是一出喜剧。但现在我们已经‘单纯够了’,如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言。喜剧终场了,并非任何单纯都是神圣的,也并非任何喜剧都是神的……我受够了浑水摸鱼,到了做网人的渔夫的时候了。”(85-86页)“单纯够了”系双关语,亦可解作“足够蠢”,典出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任何一个智者都足够蠢》(通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喜剧终场”音译自意大利语(而非注释里说的西班牙语)成语Finitala 不过《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不同于许多形式大于内容的后现代作品,叶罗费耶夫的互文辛辣得多,常常充满反讽色彩。除了文史典故、圣经文本外,红色经典、苏联宣传用语都是作者的素材库,他往往会将最端庄肃穆的官方话语放置在最滑稽可笑的场景中,强烈的反差造成一种荒诞不经的效果(这种效果有时太强烈了,以至于中译本中不得不删去一两处),前者的一本正经也就荡然无存。比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那就是不要在配方上犯错”。又如,“什么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而比这更壮丽的是……”在这两句红色经典中人尽皆知的宣言之后,紧跟着的便是作者独创的鸡尾酒配方——“迦南之膏”和“母狗下水”,而它们的配料便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堆东西(78、82页)。
强烈的批判性、讽刺性使《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相比起标新立异、另立门户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更接近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传统,难怪有急不可耐的批评家已将其称作“俄罗斯文学最后一部伟大作品”,甚至“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最后一次闪光”。自然也有不少政治热情有余、文学品位不足的批评家一心要把小说划入“异见文学”方阵,更不忘将《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与《古拉格群岛》并列为苏联时期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需知后一种表达是他们赞誉每一本书时都会用的。
不过,多数学者还是在进行着更严肃的探索,他们试图寻找小说与文学传统之间更深层的联系。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时(),巴赫金论拉伯雷的著作刚出版不久,狂欢化理论在苏联红得发紫,叶罗费耶夫无疑深受影响,小说中的许多片段都有民间文学起源;小说的标题以及用路标划分段落的形式、大量穿插的抒情与议论插笔都让人联想到感伤主义游记,尤其是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记》和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借着体裁副标题“长诗”(这个副标题在中译本中竟然被删去了),叶罗费耶夫完成了向《死魂灵》的致敬(因为果戈理也把自己的小说叫作“长诗”),而后者又是对但丁《神曲》的模仿;小说主人公韦涅奇卡一路上自言自语、自我对话都像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主人公“爱一切尘土、一切肚腹,对一切肚腹所生的都要怜悯”(页),最后又被人钉杀在无名楼道,仿佛是基督的化身,可他痴人说梦般的呓语里总是饱含真理,从这一点看,又能在他身上发现俄国文化传统中圣愚的痕迹……以上种种,还只是一眼能看出的表层联系。
可是到底为何要喝酒?——书中也许有现成的答案。“俄国所有正直的人全都这样!……是因为绝望啊!是因为他们正直,是因为他们无力减轻人民身上的负担啊!”(98页) 这里指的还是十九世纪平民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可轮到叶罗费耶夫自己这儿,醉酒就已经有了几分形而上学意义:“人活一世,也不就是灵魂的瞬间沉醉?或者灵魂的一时糊涂?我们全都像是酒鬼,只不过每人的表现方式不同罢了,有人喝得多,有人喝得少。酒对每个人的作用也不同:有人公然笑对这个世界,有人却偎在世界的怀中哭哭啼啼……我品尝过许许多多的酒,可酒却对我没有任何作用……我比所有人都清醒,我身上就是没发生过酒精的作用。”(页) 总的来说,他的世界观是虚无且悲观的:“假如世上的每个人都能像我此刻这样安静而又胆怯,像我此刻这样对一切……都缺乏信心,那该有多好啊!不要什么积极分子,也不要任何功勋业绩,更不要什么魂不守舍……假如之前有人告诉我一个并非永远需要功勋的角落,那么我同意在这世上生活到千秋万代。”(15-16页) 任何一种宏大叙事都吸引不了他,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还是他自以为笃信的基督教,最终都在他的文本里被解构、脱冕,这也是为什么以基督自居的韦涅奇卡大难临头向天使求助时,听到的只是他们幸灾乐祸的放肆嘲笑。据同时代人回忆,每当知识分子聚会时有人开始长篇大论,叶罗费耶夫都会反驳说:“我有个更好的想法,就是去商店买酒。”在叶罗费耶夫不久于人世时,一位波兰导演曾登门拍摄纪录片。这时的作家只能靠放在喉咙上的发声模拟器来说话,却依然一杯接一杯喝酒。导演问了一个颇为放肆的问题:“您的一生最后变成这样,您就不后悔吗?”作家坦然一笑:“才不呢,为什么要后悔?我很高兴这××的一生就要结束了,我朝它吐口水。” 这么看来,《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多少有几分预言色彩。小说里的叶罗费耶夫被人刺破喉咙而死,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正是酗酒引发的喉癌夺去了叶罗费耶夫的生命。这种预言甚至不局限于叶罗费耶夫一个人。作家死于喉癌后一年,苏联解体,宏大叙事的崩塌换来的并非天真者期盼的新生,而是叶罗费耶夫笔下的彻底混沌,为逃避现实生活的惨淡,人们纷纷奔向酒瓶子,只用了短短五年,俄罗斯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就从六十四岁跌到五十八岁(世界银行数据)。在这一语境下,可以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预言的不仅是作家自己的命运,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 [俄]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著 张冰译 漓江出版社 年7月第一版 页,25.00元 本文作者糜绪洋,文载年3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昆明治疗白癜风医院海口白癜风医院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ldfdj.com/haby/3874.html |
当前位置: 喉癌疾病_喉癌疾病 >我们全都是酒鬼,只不过各有不同
我们全都是酒鬼,只不过各有不同
时间:2017-2-2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预防癌症和治疗早期癌症的最有效方法每个
- 下一篇文章: 牢记这些症状,关键时刻能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