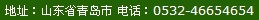|
我刚上大学没多久,就获得了一个隐秘的绰号,千杯不倒。 原因是我那时候的班主任,一位刚博士毕业留校当班主任的新手老师。新手老师奉行有教无类,在同样是博士的夫人的支持纵容下,热衷把自己家变成当代杏坛,按照寝室,家乡,兴趣等各种分类,一拨拨请同学们去他家吃饭聊天喝酒。我是他老乡,貌似和他有点兴趣将近,这种饭局酒局聊天局,蹭了不少次。也就是在这一次次持续到半夜的酒桌上,我看到周围的男女同学粉面桃腮,东倒西歪,自己还能张罗着收拾照料,才蓦地发现了这个天赋。 千杯不倒新鲜人兴冲冲打电话回家炫耀,我爸我妈特别淡定,悠悠地问:你不记得了么?你出生没几个月,你外公就拿筷子蘸酒给你尝了。 我是真不记得了…… 然而细细想想,喝倒我这些同学们这事儿吧,虽然在我意料之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我后来知道我在真酒仙那里,酒量根本不够瞧的。但是,那会儿,在我那个学霸扎堆的母校里,喝酒方面,应该没多少同学和我一样,天赋经历,全面开挂。 是的,我生而有量,家学渊源,少受趋庭之教,后有名家加持,所以百酒遍尝,千杯不倒。 我外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老太太,每周去教堂教不识字的教友一字一句读《圣经》。她已四世同堂,五个孩子各个给她准备了养老的大房间。她不,独居,喂狗,养花,种菜,去教堂,读《圣经》,《圣经》告诉她,“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得酒能悦人心”。她很快乐。她顿顿一碗自酿的白酒,一盘自种的蔬菜,微醺,饱食,熟睡。下有儿孙,上有上帝,她今年虚岁八十,准备活到一百岁。 到我爸妈这里,其实他们夫妇身怀绝技,但志不在江湖。 我爸不爱喝酒,他除了朋友聚会从来不碰酒。我妈近年来自矜温婉高雅的中年美妇,酒后脸红出丑是她的终极噩梦。近十年来,大家都自己开车去吃饭。任何聚会她都开宗明义抢着当餐后司机,借此逃过。 然而江湖都有他们的传说。我爸朋友圈基本是他的学校前同事,浙江那边,八九十年代,铁饭碗观念淡薄。这些叔叔们后来大都放弃教职,经商入仕,一个个社会老油子,酒局满场飞。我爸,这个一辈子不需要喝酒应酬的教书郎,却是他朋友圈里公认的酒量第一。他基友去温州谈生意,带上了我爸;他堂弟去非洲赚美钞,企图带上我爸……无他,但能喝尔。 如果说我爸是中年男性酒量翘楚的话,那我妈,则是跨性别的酒国名花,巾帼英雄。我妈身兼“女人自带三分酒”和外公外婆酒仙二代的双重荣誉,从出道喝酒到开车戒酒其实也就那么几年时间,但甫上沙场,就一鸣惊人,喝倒一片。近年来敌人蠢蠢欲动,妄想卷土重来,然而我妈,一个真·温婉·高雅·中年美妇,早已鸣金收兵,袅袅远去了。 正如我爸妈回忆,我喝酒方面的开蒙,可以追溯到婴儿时期蘸着黄酒的筷子。等到我自己有记忆,已经是四五岁屁颠屁颠给我外公去村口小卖部买酒的时候了。 人家的娃娃打酱油,我打酒。 黄酒盛在小卖部墙角胖鼓鼓的大肚子土陶坛里,口子是圆的,用黄泥盖子封着。我经常把整张脸贴上去往里看,阳光漏一点进去,酒是酱色通透的,盖子上的泥点扑扑簌簌浮在酒面上,一圈圈细碎的涟漪泛起,是香的,一点都不脏。 打酒勺是个连着瘦长手把的小圆开口罐子。三勺,两毛钱,满满一碗。 我小心翼翼端着往回走,小脑不发达手残小少女永远有事故,一路分花拂柳扭回去,门槛上必然一个趔趄,酒晃出来泼到我的衣服上。酒不脏衣,但是留香。 外公坐在堂屋八仙桌的上首等着我的酒。他身边的座位只有我能坐,我挪着屁股爬上长凳。外公喝着酒,排出几文大钱,问我,今天在幼儿园学到什么了呀? 我两岁就跟着我姨在她工作的幼儿园读书,一年年,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升学。我在原地混成了老童生。只有外公,坚信我天天在幼儿园学很多很多的知识,“乌龟吃雾露”,值得几个大钱的奖励。 我回答:今天学数了。1,2,5,6,8…… 外公笑,把钱给我。我把它们藏在小兜兜里,饭后跟着我姨回幼儿园睡午觉。衣有酒香,钱已入袋,我一睡睡到放学。 晚饭外公还是喝酒,晚间厨房大土灶的汤管里永远温着黄酒。黄酒热的好喝,我也能啜一小口,暖而香,有回甘。外公非常博爱,各种土酒他都爱。春天百蛇出没,抓来泡蛇酒;夏初杨梅泡酒,夏末葡萄做酒;冬天要进补,人参酒,枸杞酒正当时候。他深信,酒是好东西,每样酒都会用筷子蘸着让我尝一点。我识字未过百,百酒已遍尝。 很多很多时候,我陪着他下地劳作。他背着我,我背着酒壶。我坐在田埂头,啃一个西瓜,看着他老黄牛般一寸一寸耕作过每一分田地。他怕我无聊,隔一会儿抬头和我汇报进度:囡囡不要急,外公把这垄地翻了就好了。我摇摇头。有他在的地方,天高云淡,大地安宁永恒。我们是那么相爱的一对祖孙。 我后来出门吃饭,恨不得邻桌的剩菜都想打包带走。 别人久病成医,我外公久喝成杜康,他开始学着自己酿酒。手残少女的外公却是个手工达人,他很快就掌握了酿酒技术。几千斤粮食买回来,土制的蒸馏设备在院子里搭起来,一院子的酒香。酿出来的酒卖一些,自家留大半。不用担心喝不完,毕竟,我外公,是著名的,一天五顿酒的奇男子。 可他不是酒鬼,而是一个聪慧勤勉的本质农民。他做过一切你们能想象的江南农民会做的营生。因为他有五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要送去读书。虽然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但是在他这方面,是一直供他们,直到无法升学。我妈妈是长女,考大学两次,我二舅是次子,考大学无数次,皆未果。就算这样,他也没有停下脚步,男孩继续送去学技术,女孩继续送去学师范。他的家族后来出现了好多教师和工程师。他们再也不会他的那些农活。 他养鸡养鸭养鹅养猪养牛养羊,鸡鸭鹅都要清晨出栏,它们觅食,他捡蛋。凌晨,他需要一顿酒对抗江南湿冷的冬天。 上午他去市场卖各种农作物,午饭的桌上,他需要犒劳的一顿酒。 下午他要收拾农田,伺候作物:捞虾挖藕,制茶做酒,摘桃收瓜……休息的时候,他需要充电的一顿酒。 农村的夜晚总是来得那么早,晚饭的桌上,他需要助眠的一顿酒。 他有太多的营生需要熬夜,需要奔走,需要胆大心细。半夜,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顿酒。 他又是那么的倔强,除了在瓜田守夜,或者去外乡卖货,他从来不在外面过夜。 山里有狼,路边有坟啊! 他靠着一顿顿酒,雪夜踏雪,雨夜冒雨,良夜狼嚎月相伴,一步步走回家。清早出现在厨房,把路上买的油条泡进豆浆里,给他嘴刁的外孙女当早饭。 他,一个干瘦的小老头,背着酒壶,挂着砍刀,日日夜夜,奔走在富春江畔的富阳,奔走在钱塘江畔的杭州,奔走在桐庐的莪山畲族乡里。 畲族乡亲只有四个姓,蓝盘钟雷。一位姓蓝的大叔和我家来往四十年,我最近一次看到是前年,抱着小孙子,一车车给我家送特产。他看着我外公的遗像泣不成声:老哥啊,乡里路好了,有车了,家里房子大了,你要是还在,说什么也不让你连夜走回家了,几十公里的山路啊! 我男朋友是北京南城大杂院里长大的小学渣。他一度是正版的不良少年,很早就开始喝酒。南城自古就是酒腻子的天堂,无数的大排档小饭馆星罗棋布,他傻乐傻乐喝了快二十年,酒量其实在一瓶耳热,两杯脸红附近徘徊。去年春节他去浙江看望我和我的家人,我的舅舅叔叔们拉着他喝酒。喝的是农家自酿的红曲酒。这个北方侉子,在无知和虚荣之下夸口,两杯就被我叔叔放倒,面红耳赤昏睡在我家客房。他在奇耻大辱和百思不解中醒来,恶狠狠拎了一大桶红曲酒回北京,发誓要勤学苦练兼放倒哥们。 然而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 我近年来喝的酒,大都是因为我这个好大喜功,志大才疏,眼深酒量浅的男朋友。这个傻子经常会点太多的酒,妄想自己喝完。我会在他发觉前快速解决掉大部分。他对着空瓶,晕乎乎,费解又惆怅。 前段时间,为了支持大学师兄彭双冠一亚(此处高亮,据可靠消息说是单身!),我追了几期《中国诗词大会》。决赛那场,飞花令要求的关键词是“酒”。嗬!这有多少可说啊!谁不爱酒?谁不读诗?“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选手表现很好,师兄也是男神。那些年少时喝过的酒,读过的诗,就这么在我眼前流泻。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外公若是还在,应该也依旧是千金散尽,一天五顿。 然而六十岁出头,他就得了绝症,喉癌,发现时是中期。我们不愿意去探究这病和喝酒之间的联系。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只能进流质。我们帮他把所有的食物打成糊糊,他用白酒兑了,喝下去。我们也没有阻止。他这样,又活了十年。 “按照宗教教义,难道我们死后真的都能复活,彼此重新相见,看到所有人……” “我们一定能复活,一定能彼此相见,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互相讲述经过的事情。” 那样就好,那样就好。 外公,我还是非常非常思念您。 我现在独居在北京南边的一处小公寓里,有那么几个过不下去的深夜,酒量、自制全部远去,喝一点点就晕眩在榻榻米。 这种时候,特别容易看到外公。 您在天上还好么? 我很好。 “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号外号外,公号出炉,敬请大家扫描下面的德国强力白蚀消北京专业的白癜风医院
|
当前位置: 喉癌疾病_喉癌疾病 >我所经历的江南甘醴篇
我所经历的江南甘醴篇
时间:2017-7-1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防癌课堂10天里同个病区查出4名喉癌
- 下一篇文章: 多学科联合护理查房,齐为喉癌患者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