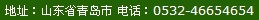|
专家详细介绍白癜风丸说明书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322968.html?ivk_sa=1024320u我认识一个名字叫幸福的男人。他是我在湖南老家时的隔壁邻居,比我大一辈,我叫他为幸福叔。今年春节,我回老家见到了他。他正挑着一担水桶去井边挑水,形若木骸,无声无息,影子般的存在。我上去打了一声招呼,递给他一支香烟,他低声“嗯”了一下,接过香烟夹在耳朵根上,便不再搭理我,径自担水去了。幸福叔以前算得上是一个爱说笑的性格开朗之人,如今则枯凋萎缩,犹如一块早已燃尽、冷却的木炭,再无半点温热。六十岁左右的年纪,也不至于如此吧?我觉得有些诧异。这里要说的就是他的故事。时针拨回到三十余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幸福叔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阳光小伙,常常未开口就咧嘴先笑,样子老实、厚道,有一把子力气,干活不惜力。因为还未婚娶,他和老父老母住在一起。他的哥哥早已成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庆瓜跟我年龄相仿,几乎天天在一起玩。庆瓜的爷爷奶奶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给小儿子找媳妇。在农村,幸福叔的岁数不算小了,偏偏多次相亲,均不成功。家里条件不好,但也不算穷。要是盖上二层红砖楼房,娶媳妇肯定不成问题了。那时,一个村里也就一两户人家盖了红砖房,绝大多数是住土砖瓦房。盖红砖房不容易,家里积蓄不够,显然是不行的。幸福叔家是土砖房,要盖新房,还得攒上几年钱。屡屡相亲不成,一家人多少有点郁闷。庆瓜爷爷脾气暴躁,平时爱坐在屋檐下的竹躺椅里,大口大口抽旱烟。一天因小事冲着幸福叔破口大骂,而幸福叔也一改温驯脾气,把老头子连人带躺椅,一把推进了门前的臭水池里。庆瓜爷爷在臭水池里扑腾,比落汤鸡更狼狈,挣扎着爬上来接着破口大骂。庆瓜奶奶一边给老头子洗脏衣,一边直抹满脸老泪。没能盖新房,可以想其他路子啊。年的秋天,一天放学后,我刚回到家里。庆瓜就匆匆跑来找我,说叔叔家买了一台电视机。那时,村里还没有人家有电视机,一听说幸福叔买了电视机,纷纷过来瞧个稀奇了。那是一台火红色外壳、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幸福叔像抱一个婴孩般,把它从纸箱里小心翼翼抱出来,轻放在柜子上,然后转弄着天线调收频道。我们这帮小孩,看得聚精会神。当荧屏画面出现时,屋子里全都欢呼起来。那天为了多看一会儿电视,我坚决不吃晚饭,对妈妈催我回家的喊声置若罔闻。《童年往事》图片买这台电视机大约要五百元,对农家来说花费不菲。庆瓜奶奶咬了咬牙,把栏里的一头肥猪卖了,还卖了几百斤谷子,加上女儿给的一些钱,总算把电视机抱回来了。幸福叔觉得还不够,又掏钱去买了一台录音机。其时,大部分村民家里,最高端的电器不过是手电筒。幸福叔家同时拥有电视机、录音机,气派立即上去了。过年的时候,他从城里带回几盘磁带,往录音机里一插,音量调到最高,欢快的歌声在空气里荡漾,四邻都听得清清楚楚。说媒的人也多了,庆瓜奶奶往日一脸的愁苦,也绽出笑容了。然而,每次相亲后,不是人家姑娘不满意,就是幸福叔不满意,一年多下来,竟然还是没有定下对象。庆瓜奶奶又恢复了一脸愁苦。庆瓜爷爷又常常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破口大骂。幸福叔的反应也没以前那么激烈了,也就默不作声。但幸福叔还是每晚把电视机抱出来,摆到外面宽阔的晒谷场上,方便邻里大伙儿看。只要不停电,每晚场地里都要围满老少几十号人,没带凳子的小孩甚至爬上树,坐到树杈上看电视。电视剧《霍元甲》、《陈真》、《上海滩》等,那时就是我们心中的最爱。有一次,我在家练毛笔字,一时兴起,提笔蘸墨来到幸福叔家,在门中央写上《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几个墨黑大字。字写得歪歪扭扭,墨汁却渗进了木头,像一排乌鸦般丑陋。幸福叔用抹布蘸水,怎么擦也擦不掉。但他也只是笑笑而已,对我并未有任何责怪。在这个时期,村里的太平叔得了喉癌。癌症很可怕,大伙儿都这么传着。太平叔住在大屋院子,那里有几排凹字形的祖传瓦房,好几户人家拥挤着住在一块。我们这帮小孩,常去院子里玩。每户人家平常也不关门,我们就在各间老屋子里穿梭,玩捉迷藏的游戏。太平叔已婚,跟媳妇文英感情很好,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小武。当初,在太平叔新婚之后,我们这帮小孩还去他家窗下偷窥。他和媳妇有时躲在蚊帐里亲热,一发现我们躲在窗下,就跳下床来撵我们。他为人亲和,从不骂脏口,平时爱鼓捣钟表。文英婶身材丰满,不算漂亮,但也眉眼含春,待人也热情。美满的三口之家,却因癌症蒙上了阴霾。文英婶天天熬药,而太平叔都进不了食了。没过多久,太平叔就死了。去世的那一天,他坐在椅子上,骨瘦如柴,低垂着头,面色惨白如纸,如木偶般被抬到停棺材的堂屋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模样,却一点也不害怕,只是觉得有点古怪。文英婶哭得死去活来,把额角都撞出血来了。孤儿寡母,以后不好过日子呀,左邻右舍这么看在眼里。一个月后,经村里的老太太热心撮合,文英婶同意改嫁给幸福叔。没过几天,她带着小武搬进了幸福叔的家里。庆瓜奶奶甭提多高兴了,整天地头、灶头忙着,不让文英婶干一点家务活儿。幸福叔也是满面春风,即便还没过年,就把录音机拿出来放音乐。邓丽君《回娘家》的欢快歌声,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回荡:“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里流水得儿哗啦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儿她走得忙又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一切尽在不言中,也就剩下领证办酒的事儿了。也许是冬天的夜里冷,老人受不了凉,庆瓜爷爷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天,竟然去世了。喜事还没办,丧事得先办了,令人沮丧。老头子习惯天天嚷嚷,嘴里舔着一根旱烟,不那么招人喜欢,但一旦没了他,周围好像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幸福叔和一家人披麻戴孝,未成婚的文英婶也穿了孝衣,家里气氛也不活泼了。电视还是放给全村人看,但录音机已经悄悄收起来了。庆瓜爷爷才入土为安,村里又出事了。太平叔有一个胞兄,平时在铁路上工作,一直没有婚娶成家。听闻弟弟去世,他赶回来后,精神受到刺激,从此有点不正常。也不去上班了,常常一个人在老屋子里发呆,偶尔出来走走,也显得精神恍惚。有一次,他把邻居的一间茅房放火点着了,虽然被及时扑灭,没有闹出大事,但村里人都说他疯了。在庆瓜爷爷去世后不久,一天下午,我们又去大屋院子玩捉迷藏。在太平叔家里陡然发现他的兄长像一只瘦鸡一样悬在房梁上,双腿一动不动,眼珠子鼓凸,舌头伸得老长。黑魆魆的老屋子里,光线昏暗,透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那一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可怖,吓得晚上睡觉蒙在被子里,大气不敢出一声。之后,我再也不去太平叔家玩了,总感到那里似乎有一双莫名的眼睛在黑暗中盯着。太平叔还有一个已嫁的妹妹,丧事就由她来操持了。文英婶带着小武,也去尽份内之事,又是披麻戴孝。按习俗,寻短见的过于晦气,丧事办得潦草,没有办酒席,来客也无多安慰,乐手们勉强吹吹打打一番,几名壮汉把棺材匆匆抬到山上,挖一个坑埋掉完事。此时,村里的流言蜚语已经起来了。有爱嚼舌头的妇女私下传说:文英婶是一个大扫帚星,是一个狐狸精,先是克死了丈夫,来到幸福叔家里又克死了老头子,还接着克死了丈夫的哥哥。这样的女人,谁娶进家里谁倒霉。又有爱嚼舌头的男人私下传说:这个女人命太硬,幸福对她百依百顺,怕是制不住她,还没结婚就闹成这样,以后难说了——过年开春之后,幸福叔准备领证、办酒席,名正言顺把文英婶娶过来。提前两周就置办了一些喜糖、烟酒、鞭炮,新婚用的镜子、浴盆、箱子等也买了回来。大伙儿虽然心里狐疑,但也等着吃喜酒了,不停地问哪一个日子?幸福叔笑着答就快了。庆瓜奶奶仍然忙前忙后,还是满心欢喜。选了一个黄道吉日,两人换上新买的衣裳,一大早前往乡政府去登记了。快到的时候,文英婶突然对幸福叔说,自己想先回娘家一趟,告诉她老娘一声,马上就赶回来。幸福叔要求陪同前去。但她说不用了,办完喜酒他再去更好,而且自己最多两三小时就回来。幸福叔觉得有理,就依她言,约好到乡政府后等她,顺便逛了好一会儿集市,买了一些酒肉,准备登记完回去后炒几个好菜,自家里先庆祝一下。那一天等到黄昏,也不见文英婶回来。他急了,顾不得那么多,就大步直奔文英婶娘家。到了后一问,原来她根本没回娘家,已经不知所踪。庆瓜奶奶煮好了饭菜,一直没有吃饭,在等儿媳回来。半夜里,幸福叔回到家时,阴沉着脸,像泄了气的皮球。庆瓜奶奶问知原因,失声大哭起来,把邻居都惊醒了。而小武在隔壁屋子里,一个人睡得很香很沉,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妈妈抛弃了。文英婶无情地抛弃了幸福叔、小武,独自跑到远方某个地方去了。村里又有私下谣言,说幸福叔那方面不太行,不懂得睡女人,文英婶对他很不满,因此就跑了。很多年内,她杳无音讯。后来听人说她嫁给了一个铁路工人,但从来没回来看望一下儿子。小武八九岁的时候,每当别人提起妈妈,他就狠狠地说,她早就死了。幸福叔没能结成婚,喜酒自然也黄了。太平叔的妹妹,也就是小武的姑姑,把小武接到她家去了。家里顿时冷清下来,母子俩好生凄凉。那以后,庆瓜奶奶变得更加苍老了,像一块焦黑的炭灰,脸色再无光彩。喜糖放在柜子里,对小孩很有吸引力。趁奶奶、叔叔在地里干活,庆瓜于是偷偷掀开柜子,一次次把喜糖拿出来,与我们这些小玩伴分吃。不到两个月,喜糖被我们全部偷吃光了。当我们把最后一颗糖塞进嘴里,感到百无聊赖时,庆瓜从家里的床底下发现一面铜锣,于是扒了出来,当当当地敲起了锣。锣声把奶奶引来了,只见她脸色难看,责怪了庆瓜几句,要他马上别敲了。原来,根据老家习俗,家里若有人去世,家属便敲着铜锣去江里取水,回来给死者净身。庆瓜敲得起劲的铜锣,正是此前他爷爷去世时用过的。这锣声自然不吉利,像是一道谶言,让他奶奶感到心惊胆颤。六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暗了下来,父母还在地里干活,没有回来。我煮好了饭,正在门前的桃树下坐着,庆瓜奶奶捧着一袋熟李子送过来,塞进我的手里,说是给我吃的。我收下后,取出一颗就嚼了起来,李子的果肉有点甜而酸涩。她见我吃得欢,满脸木刻般的皱纹绽开了,随后驼着背慢慢走回去了。很多年后,我回忆起来,才觉得她当时的笑容和背影,竟是无以形容的苍老、凄凉。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告诉我,庆瓜奶奶昨晚去世了。庆瓜奶奶一个人住在一间老屋里,夜里就喝下大半瓶敌敌畏,喝农药后毒发,双手痛苦地敲拍着门。庆瓜妈妈夜里起床小解,听到婆婆屋里的响动,就赶过去瞧。她还以为是黄鼠狼来叼鸡呢?一看婆婆的样子,吓得赶紧叫醒丈夫、幸福叔和邻居。大家跑来看时,庆瓜奶奶躺在地上吐着白沫,已经不行了。等我跑去看时,庆瓜奶奶已经入了棺。一口未油漆过的薄皮棺木,停放在屋厅里。隔壁的屋子里还残留着一股刺鼻的农药气味。我感到很意外,但又什么都说不出来。跟大人们严肃的表情完全不一样,我和庆瓜这些孩子,一点也不感到悲伤,好像觉得这挺自然的。庆瓜奶奶的墓,跟他爷爷的墓紧挨着。他爷爷的坟头还没有长出多深的茅草,两座坟看上去都是新的。庆瓜奶奶为什么要喝药自尽呢?现在也说不清楚。老父老母相继过世,幸福叔彻底成了一根光棍。一个人下地干活,一个人做饭洗衣,煮一锅饭要吃上一天。因为接连办白喜事,花了一些钱,庆瓜妈妈也对幸福叔有怨言。家中这般光景,自然是没人再登门说媒了。幸福叔渐渐成了四邻村里有名的光棍。如此过了两年,在亲戚的介绍下,幸福叔前往广州一家猪饲料添加剂厂打工。这比在家种地要强多了,辛苦干了两年,多少也算攒了一点钱。之后,他又回来准备盖红砖房了。自己雇人打砖、烧砖窑,拆掉了老土砖房,盖了四间红砖平房。这个时候,红砖房已经不稀奇了,村里很多人家都盖了新房。电视机更是普及,年轻人还买起了VCD,再也没有人到幸福叔家看电视了。他住进了新房,虽然偶尔有人来做媒,但还是没有谈成。随着年岁渐长,幸福叔娶媳妇的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形影相吊、茕茕孑立。我上初中后,放寒假回家,就跟他借录音机来放歌。他倒也痛快,把那台积压已久的录音机提给了我。当时我哥已经上大学,从学校带回了《人鬼情未了》《风月俏佳人》之类的外国歌曲磁带,我就用幸福叔的录音机,听起了这些外国歌,还听香港四大天王的流行歌曲。有时在家一边烧火做饭,一边高声放歌,烟熏火燎中,《人鬼情未了》深情缠绵的歌声飘荡。幸福叔还去过广州打工,但后来那家添加剂厂倒闭了,他又回家种地了。农村单身汉的生活一天天重复,似乎也没有太多可说。那时种地又不挣钱,农村税负太重,有一年母亲又生病,我家的经济陷入窘境,一学期的学费全指望栏里养的一头猪了。那头猪也挺争气,噌噌地长,体肥膘厚。正好几里地外的邻村有一家人办白喜事,需要买一头猪。父亲就请来屠夫把猪宰了,分成两担挑去邻村。幸福叔前来帮忙,挑了一担猪肉走在前面,我挑了一担跟在后面。每担都重达一百多斤,幸福叔的那担要多重四五十斤。恰逢夏天下暴雨,乡村小道上全是泥。幸福叔戴着斗笠,赤脚踩在泥水里,一步一步挪动。我也戴着斗笠,走在后面踉踉跄跄。我俩唯恐摔倒在泥地里,浑身都湿透了。那幕雨中艰难前行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再过几年,我也上大学了,离开了老家。因回家次数稀少,对老家的人事也渐渐疏远。毕业工作后,还是如此。偶尔返乡,也是匆匆待几天就走,跟幸福叔自然也谈不上有多少交流,甚至根本见不到面。这十余年间,他把红砖房又加盖了一层,还里外装修了一番,窗户也是铝合金的,看起来还不错。他还是一个人过日子。大屋院子的老屋早就无人居住,在风雨中一间一间逐渐倒塌了,沦为一摊砖瓦废墟。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家,也早已陆续搬走了。小武的姑姑一家子,也带上小武去城里捡废品去了,已经多年没回村里。今年春节还乡,也仅仅见了幸福叔一面而已,我们并无再多交谈。而他每天都沉默寡言,平时大多躲缩在家里,不出来跟其他人说话,包括他的兄嫂一家。大年初一,按照习俗,邻居们纷纷相互贺喜拜年,只有他闭门不出。我觉得诧异,于是向邻居们打听原因,她们说了这样一个简短的故事。原来,三年前,幸福叔曾经在县城的一家糖厂打工,跟厂里的一位中年女工相熟。这位女工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她比幸福叔小十几岁。幸福叔很疼爱这个孩子,经常给他买好吃好玩的东西,还时常帮衬这位单亲妈妈。日久生情,在糖厂的同事们看来,他俩是好上了,结婚应是水到渠成之事。那一阵子,幸福叔干劲很足,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回家请人把房子装修好了,完全符合农村婚房的标准。房子装修完了,但这位单亲妈妈却私下悄悄离开了糖厂,带着孩子去广州打工了。幸福叔得悉后,也马上赶往广州,好不容易找到了她。这位单亲妈妈也还算热情,给他开了一间宾馆房间,请他吃特色美食,在广州游玩了几天。之后,她买了一件新衣服和一张返程车票,塞给了幸福叔,委婉拒绝了他的求婚。幸福叔独自默默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回来后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彻底丧失了精气神。他不再跟大家说笑,变得沉默无言,甚至亲戚邻居跟他打招呼,他也毫不理会。他还是独自种地种菜,也去赶集卖东西,偶尔会说几句话,但大多时候几乎完全哑寂,形同一个影子。由于单身无后,按照五保户的养老政策,幸福叔可以去镇上的养老院,村委会也给他办了手续。但他并不愿意去。他开始骂人,骂所有的人,尤其是骂村里那些神气显摆的人。被骂的人装聋作哑,全当没听见。大伙儿早已把他当成了疯子。幸福叔还每天早上到后山上,捡一些枯枝败叶,生起一堆火,常常被青烟呛得涕泪交流。邻里也没人管他,也没人问他生火干什么。有一点确定无疑,那一堆野火,点燃,熄灭,又点燃,却永远也温暖不了他心中的寒冷,他将注定在孤独中一天天老去,直至最后死去。 文/南焱 编辑/刘成硕 运营/胡雅婷 被偏爱的孤女的一生 镜相 成为母亲,成为单身母亲 镜相 拼杀在都市的小镇“后浪”:曾做三份兼职,曾背百万债务镜相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当前位置: 喉癌疾病_喉癌疾病 >他叫幸福,名字却像个诅咒镜相
他叫幸福,名字却像个诅咒镜相
时间:2021-11-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新刊速递年陕西文坛第
- 下一篇文章: 癌症病人怎么吃中读书笔记